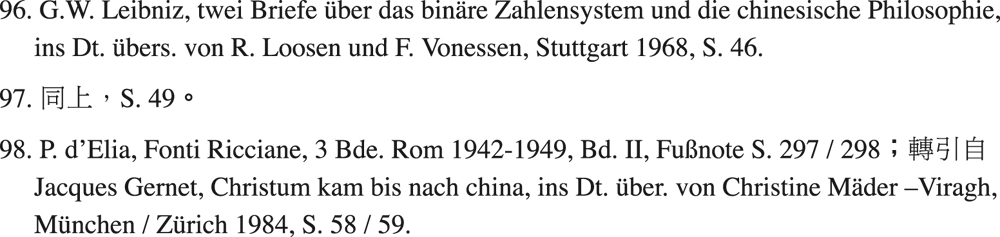陸
利瑪竇旳《天主實義》是繼羅明堅的《天主聖教實錄》以後,又一部用教理問答式對話寫成的漢文神學著作,但它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卻遠非後者所能比及。它最初以《天學實義》為題,於1595年在南昌刻印發行,後改稱《天主實義》,於1601、1604年兩次在北京重刻,1605和1606年間又在杭州重刻。利瑪竇死後,李之藻(1569-1630)把它收入他於1629年編輯出版的《天學初函》。在此期間,又流傳到日本、越南和朝鮮。後來,法國神甫雅奎(ClaudeJacques,1688-1728)把它節譯成法文,以 ![]() (《中國學者和歐洲博士對話錄》)為題,收入Choix de lettres edifiantes(《參考文選》Bruxelles 1838)。不過,此譯文過分自由,大傷原意。
(《中國學者和歐洲博士對話錄》)為題,收入Choix de lettres edifiantes(《參考文選》Bruxelles 1838)。不過,此譯文過分自由,大傷原意。
嚴格地講,這不是一部教理問答;因為它所討論的問題並非基礎教義,而是,如利瑪竇所說的,那些可以用自然神學或人的理性推論、用現有的儒學概念所能夠證明的基督教信條。如:上帝——天地的創造者、靈魂不死、天堂地獄的存在等。《天主實義》的重點是對於被視為傳佈基督教信仰的障礙的釋、道兩教和宋明理學的批判,這佔了近一半的篇幅。本文討論的重點是利瑪竇如何用儒家概念論證基督教信條,反過來講也可以說,他如何給儒學概念以新的、基督教的解釋。
一、對「上帝」的新解釋
上帝又稱為帝、天帝,是中國古代對至上神的稱謂。見於甲骨卜辭、戰國策、詩、書、易、禮等文獻中。利瑪竇主要用上帝這個大量出現於《詩》、《書》等儒家經典中的概念,來比附基督教信仰的Deus,即耶穌會譯稱的天主。他首先認定,「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接著,他援引儒家經典論證說:
「《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予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雅》云:『維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曰:『天子親耕;粢盛柜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金縢》周公曰:『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為上帝可知。」
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
「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64.
在對上述引文的討論以前,首先有必要說明一下關於Deus的翻譯問題。耶穌會內外對此曾有過幾度爭論,最後確定,捨棄「上帝」,只用天主,以避免與古代中國人信奉的至上神相混淆。「天主」一詞也是借用的中國原有詞語,《史記•封禪書》曰:「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另外,也不准用「天」來稱謂Deus,因為有的耶穌會士和後來在「禮儀之爭」中反對利瑪竇的多明我會教士認為,中國人所敬的天是仰面可見的蒼天,是物質性的。這就是在上述引文中利瑪竇兩次把上帝與天區分開來的原因。實際上,這種區別是不必要的,因為「天」的含義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天帝,亦即上帝。如《書•泰誓上》:「天佑下民。」1704年11月20日教皇格勒門——(Klemens XI,1700-1721年在位)頒發「聖諭」正式確認使用天主,禁用上帝和天。鴉片戰爭後傳入中國的新教則接受了上帝這個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從基督教歷史上看,利瑪竇借用當地民族原有概念稱謂基督教所信仰的神的作法完全來自使徒保羅。《新約•使徒行傳17》載,保羅來到雅典,看到滿城偶像心裡十分難過。他在會堂、廣場不斷與人發生爭執,人們不相信他傳佈的耶穌和他復活的福音。保羅站在亞略巴古議會會堂說:「雅典居民們,我知道你們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宗教熱情,我在城裡到處走動,觀看你們崇拜的場所,竟發現有一座祭壇,上面刻著:『獻給不認識的神。』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就是這位你們不認識、卻在敬拜的神。這位創造天、地和其中萬物的神乃是天地的主。」保羅使雅典人認識他們所「不認識的神」,而利瑪竇則是讓中國人認識中國古代經書記載著而為他們所忘記的上帝,兩者都是為了讓當地人在他們所熟悉神靈的名義下信奉基督教的神。
在中國宗教史上,所謂「老子化胡說」與利瑪竇的「上帝即天主」說,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一度被視為是黃老神仙術的一種,於是出現「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說;佛教自己也附於黃、老,以便在中國傳統信仰的名義下傳橎自己的教義。看來一種外來宗教要得到傳播,迎合和憑靠當地思想文化傳統,是一條必由之路。
二、對「仁」的新解釋
「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它在《論語》中出現了一O九次,孔子對它的解釋也因人而異。張岱年先生認為孔子所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6•3》)便是他規定的仁的界說65.。今從其說立論。在中國歷史上,人們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它作出解釋,如孟子釋仁:「仁者,人心也。」66.這與他強調個體人格修養是一致的。董仲舒:「仁者,愛人之名也。」67.他強調是施愛予人。朱熹:「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68.他解釋說:「『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69.他引用程頤的話說:「程子曰:『心如谷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70.他從他的理學出發,把仁看成是先天觀念。利瑪竇對這種引古籌今的作法是很熟悉的,他曾說過,在中國「凡希望成為或被認為是學者的人,都必須從這幾部書(按指五經、四書)裡導引出自己的基本學說」71.。也許可以說,利瑪竇主要不是從中引出,而是向裡加進自己的學說,他解釋說:
「夫仁之說,可約而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為天主。」72.
他在他的《廿五言》中對此作了詳細解釋:
「夫仁之大端在於忝愛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實有,又信其至善而無少差謬,是以一聽所命,而無俟強勉焉。知順命而行,斯謂之智……君子不獨以在我者度榮辱、卜吉凶而輕其在外,於所欲適欲避,一視義之宜與否。雖顛沛之際,而事上帝之全禮無須臾間焉。」73.
在這短短的一段話裡,利瑪竇從仁即愛上帝這一全新命題出發,也給予了信、智、義、禮以全新的內涵,這種近於文字遊戲的牽強解釋是很明顯的,無須贅言。
三、對「孝」的新解釋
利瑪竇對孝的解釋,可以說是一個儒學與基督教義合一的命題,他寫道:
「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一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君之旨者,不孝子也。」74.
他在這兒把對神的敬、對君的忠和對父母的孝都列在了「孝」這個概念之下。不過,這跟孔子講的「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17•9》)倒也是一致的,只是他外加上了敬神一項,而且把它提得高於其餘兩者。他解釋說,假如「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顧其上,其為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為孝也」。但是,「若從下者違其上者,固大為不孝也」75.。表面上看來,利瑪竇似乎是把神命、君命置於父命之上,實際上是把神命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接著他補充說,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之,乃無上共君也。世人弗養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76.。這樣的孝跟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13•8》)已大有區別。但是,它也不同於耶穌對他的門徒們的訓誡:
「如果有人到我這兒來而又不鄙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就不能作我的門徒。」77.
相比之下,利瑪竇對於中國人的態度是很寬容的,他認為「有愛父母不為天主者,茲乃善行,非成仁之德也」78.。他甚至容許基督徒祀祖祭孔,他說,這種在死者墓前上供的作法似乎不能指責為瀆神,而且也許並不帶有迷信色彩;因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孩子們以及沒有讀過書的成年人,看到受過教育的名流對於死去的父母如此崇敬,就能學會尊重和供養自己在世的父母」79.。他指出,祭孔是為了「表明他們對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學說的感激」,正是這種學說使他們得到學位,從而使國家得到大臣、具有公共行政權威。當然,利瑪竇說,基督徒如果「以救貧濟苦和追求靈魂的得救來代替這種習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80.。
四、對「誠意」的新解釋
「誠意」是《大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書中解釋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6》)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人應不斷純潔自己的意念,達到善善因其為善、惡惡因其為惡這樣一種高度自覺的精神境界。這兒的「意」是個一般概念,按照朱熹的解釋,即「性之所發也」。「誠意」即「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81.。利瑪竇混淆一般和個別概念提出論題:「解釋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為善惡」。在這個標題下的一章中有一段對話:
中士曰:「夫因趨利避害之故為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君子為善無意,況有利害之意耶?」
這兒的「無意」用得令人費解,從上下文看應是指沒有個人功利目的,「意」在這兒含義是具體的、有所指的。接著,利瑪竇讓西士對答:
西士曰:「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儒學無誠意不能立夫!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幾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82.
利瑪竇用「誠意」駁斥「無意」、「滅意」,顯然是耍了一個小小的詭辯術:偷換概念。即把「誠意」之意——一般概念——與「無意」之意——個別概念——等同了起來,從而在堅持「儒者之本論」的名義下傳佈基督教義。其實,利瑪竇應該肯定他所理解的那種「為善無意」的,因為為善因其善、避惡因其惡,這也是基督教徒所追求的完美品格。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在他的著名神學論文《論人類教育》中曾經指出:「它將到來,它一定會到來——那完美的時代。到那時,人的理智越是深深感到有一個日益美好的未來,他便越是無須向未來乞求他的行為的動力;因為他行善只因其為善,而不是為了企圖由此得到任何報償,而以往這種報償卻僅僅能夠吸引和捕捉住他那疑惑不定的目光,使之認識到更高的內在報償。」83.利瑪竇不是啟蒙思想家,在他那兒人對於健康理智和完美品格的追求並不佔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首先成為教徒,甚至為了證明天堂地獄之存在,他倒是可以犧牲這種追求的。
五、在人性論上與朱熹相遇
利瑪竇儘管反對宋明理學,但他的人性論觀點卻與朱熹極其相似。他說:
「若論厥性之體與性,均為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為主,則俱可愛可欲,本善無惡矣。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我或有可愛,或有可惡,所以異。則用之善惡無定焉,夫所謂情也。」84.
試比較以下朱熹的說法:
「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混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85.
朱熹又把天賦予人之性稱作「天地之性」,這相當於利瑪竇所稱天主「所化生」之性,兩者都認為這是善的。朱熹把「理與氣雜」,「聚而成質」的個體之性稱作「氣質之性」,這種性是「善惡有所分」的86.,這就是利瑪竇所稱的「善惡無定」的「用機」。我們看到,利瑪竇恰當地使用中國哲學中的範疇「用」來表示人性之已發。但是朱熹和利瑪竇畢竟各有其不同的哲學傳說,前者的人性論實際上繼承董仲舒的聖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人性界說,和王充的性三品說,他的新發展在於他以理釋性並從他的理氣本體論出發,把人性分作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從宇宙本體上論證人性。利瑪竇的人性論跟把人性看成是神性的經院哲學不完全相同,他從亞理斯多德的靈魂階梯說出發,更重視人性中的理性,他說:
「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於金石,曰覺以異於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87.
在另一地方,他又說:
「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為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覺物情,是為禽獸之魂;上品曰靈魂,以兼生魂、覺魂,能扶之長大及覺物情,而又能俾所賦者推斷事物、明辨禮義,是為人類之魂……凡物非徒以貌相定本性,乃惟以魂定之。始有本魂,後為本性。」88.
不知利瑪竇是否讀過《荀子》,他在這裡用以界定人性而間接引述的亞理斯多德《論靈魂》中的論點,與荀子幾乎完全一致,荀子寫道: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89.
所不同者,荀子多用了一個中國哲學所獨有的表示「聚以成質」的概念「氣」,他在這兒是給人下定義。亞理斯多德是根據生命的三個階梯劃分三種不同品格的靈魂。利瑪竇則把後者作為他界定人性的根據。這兒真是巧遇,利瑪竇在人性論上與朱熹相遇,前者借以界定人性的亞理斯多德的靈魂階梯說,又與荀子為界定人類屬性而對自然所作的分類相遇,從而利瑪竇又間接地與荀子相遇。
六、與宋明理學對立
上文提到,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用了大量篇幅批判釋、道兩教和宋明理學。在某種意義上講,《天主實義》可謂一部褒儒眨佛、尊古儒排宋儒的代表作。利瑪竇所攻擊的這些對象,其間差異儘管很大,但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尤其佛教和理學都有各自的描述和論證世界生成、萬物起源的理論體系,而且,這些體系從根本上是與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和上帝創世說相對抗的。關於利瑪竇對佛、道的攻擊,限於本文論題,不可能作深入討論,僅錄其言,說明他這種態度在極大程度上是出於一個宗教徒對異教的本能偏見:
中士曰:「拜佛教、念其經全無益乎?」
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維此異端……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有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犯罪乎?」90.
在對理學的批判中,利瑪竇首先將之與古儒對立起來,他借西士之口說:
「余雖末年入中華,然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於天地之主宰,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為主宰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91.
然後,他針對理學的本體概念「理——太極」主要提出了三個反對理由:
(一)「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他的理由是「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而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若以虛理為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92.。
(二)「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他說:「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他對天主和理作了比較:「天主雖未嘗載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合眾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匯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為自立之類乎?」93.
(三)「理卑於人,理為物而非物為理也」。他引用孔子的話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他的結論是:「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94.
利瑪竇在這兒所玩弄的概念遊戲,一眼便可看穿。他將作為精神本體的理與作為事物內在秩序的理混為一談,然後以後者的局限性來否定前者作為本體存在的無限性。上文提到,利瑪竇是用自然法(lex naturalis)解釋古代中國人的道德行為規範,是以自然神學觀點評價儒家的倫理思想的。但從他對理學的態度看,他對此並不認真。自然法與自然神學存在著某種聯繫,聯繫的紐結便是理性。
利瑪竇應當知道,對於自然法的解釋,基督教神學家是從斯多噶派接受過來的。斯多噶派認為,自然這個概念與最高理性的永恆法則(lex aeterna)是一致的,因此永恆法則也就是確立於人的自然理性之上的法則,即自然法(lex naturalis)。中世紀基督教早期神學家,接受了斯多噶派的自然法觀念,不過,他們把永恆法則改為創世上帝,作為永恆法則的制定者,而把自然法解釋為置於人的本性中的基本秩序。
但是,關於永恆法則中起主導作用者是理性還是上帝意志,一直是中世神學爭論的一個問題。自然神學的提出者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在永恆法則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理性,而不是上帝意志。晚期經院哲學家的看法則相反,把主導作用歸之於上帝意志。利瑪竇既然承認,古代中國人在自然法中得到拯救,既然認為中國古經書中的上帝即基督教的Deus,既然發現儒家經典中存在著某些與基督教義相近的東西,那麼,他本應與從斯多噶派到托馬斯•阿奎那這條軌跡相平行,從古經書,尤其從《易經》到朱熹連成一條線。他當會發現,不論從那層意義上解釋,朱熹的作為解釋世界的精神本體和社會倫常秩序的道德本體的理,恰恰可以與上述永恆法則(lex aeterna)或者上帝(Deus)相比。
讓我們看看那位不懂漢語,更不能直接閱讀漢文文獻的萊布尼茨在閱讀了利瑪竇的繼承人龍華民(Nicolas Longobaldi,1559-1654)關於朱熹的理概念的極度扭曲的敘述以後,對理的理解,他寫道:
「根據所有這一切,人們為什麼不說,理即我們的上帝,即存在、甚至事物本性之終極或者原初根據,即寓於事物之中的所有善者之源,即安那克薩戈拉95.,以及其他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分別稱之為vouc和mens的原初理性呢?」96.
萊布尼茨立即看出了朱熹的理之精神屬性和無異於基督教上帝的品格。但是,利瑪竇卻沒有達到這個認識,原因很簡單:他是傳教士,他把上帝看成是信仰對象,而作為啟蒙思想家的萊布尼茨除了把上帝看成信仰對象以外,更認為上帝是解釋和論證世界作為世界而存在的充足理由。固然,利瑪竇也把理與上帝相比,但是比較的結果是他用上帝來取代理;萊布尼茨則不然,他從兩者品格的相近,進而把兩者相提並論,認為兩者都是絕對本體。他說:
「根據所有這一切,難道人們不可說,中國人的理就是我們在上帝的名義下所敬拜的那個絕對本體嗎?」97.
柒
現在,我想讓利瑪竇本人把我們領回到我們開始討論他的儒學研究目的時的起點上。他在1604年致耶穌會會長的一封信中寫道:
「這個太極說是新的,是五十年以前(按:此處為『五百年以前』之誤——引者)方才提出來的。如果仔細探討一下,它在某些方面是與對上帝曾經有比較清晰的觀點的中國聖哲相矛盾的。按照他們的說法,我認為它不是別的什麼,而是我們的哲學稱之為第一物質的東西,它絕不是一種本體存在。他們說,它非物,而是萬物的一部份。他們說,它非靈,也沒有理智。儘管有幾個人認為它是事物的原因,但他們指的卻不是本體性的或者是具有理性的東西。這個原因毋寧說相當於被原因引起的原因,而非原因之原因。現在,許多人有另外的看法,發表了許多悖理的意見。因此,對我們而言,最好似乎不是在本書中(按指《天主實義》)攻擊他們,而是改變他們的話的原意,使之符合上帝概念。這看起來不像是我們跟著中國作者走,而更像是我們讓他們跟著我們的觀念走。假如我們攻擊這項原則(太極),那些治理著中國的學者便感到受到了極大的侮辱。所以,我盡力對他們關於此一原則的解釋,而不對原則本身提出質疑。如果他們最終認識到,太極是本體性的、具有理性的、無限的初始原則,那麼我們雙方便取得了一致:這就是上帝(Deus),而不是指別的什麼。」98.
宗教的激情、為信仰而獻身的精神、為達到便於傳教的目的,推動著利瑪竇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學說。然而,宗教偏見和實用主義的態度卻又阻礙他對儒家學說的發展進程作出科學、客觀的分析,使他無法將儒家學說按其本來面貌介紹於歐洲公眾之前。這是令人遺憾的。不過,這是當時許多人都無法衝破的時代的和意識形態的局限造成的。我們不應苛求於一位生活於四百多年以前的學者,何況他又是一個傳教士呢。
注釋
- 參閱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1, Camebridge / London / New York 1979, P.168-193;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篇第四、十一、十二、十三各章,岳麓書社,1988年長沙,第64-76、147-185頁。
- 參閱J. Needham,同上書P.154-167;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海,第20-22頁。
- Gaius Plinius Secundus, Historia naturalis (
 ), ubers. von H. Eppendorf, Strassburg 1543, S. 193.
), ubers. von H. Eppendorf, Strassburg 1543, S. 193. - 轉引自沈福偉,第21頁。
- Eusebius, Praeparatio Evangelica, VI, 10,轉引自J. Needham, vol. 1, P.157.
- 同上,P. 158。
-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象。
- Origenes (Amadantius), Von der Wahrheit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wider den Heiden Celsum, ins Dt.
 s. von J. L. Mosheim, Hamburg 1745, S.800.
s. von J. L. Mosheim, Hamburg 1745, S.800. - 同上,S. 801.
- 轉引自Wolfgang Franke, China und Abendland,
 1962, S.6;方豪:中西交通史,第365頁。
1962, S.6;方豪:中西交通史,第365頁。 - 參閱Heinrich Boehmer, Die Jesuiten, neu hrsg. von Kurt Dietrich Schmidt, stuttgart 1957, S. 132.
- 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北京,上卷,第60頁。
- 同上,第61頁。
- 同上,第62頁。
- Knud 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 in : China Mission Studies ( 1500-1800 ), Bulletin 1, 1977, P.2-11.本文論及羅明堅四書譯事一段,主要參考了該文所提供的材料。
- A.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ancienne de Chine, Shanghai 1932, S. 21.
- P. Couplet,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 1687, S.1.
- Matteo Ricci / Micolai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Augsburg 1615, S.29.
- P. Couplet, S.1.
- 朱熹:大學章句•1。
- P. Couplet, S.1.
- 朱熹:大學章句•1。
- P. Couplet, S.1.
- 同上。
- 轉引自K. Lundbaek, P.9, reference 26.
-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982頁。
- 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第971頁。
- David Mo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64.
- 30. 同上,P.63.
- 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之影響,1983年,福州,第68頁。
- Tacchi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II, 117,轉引自K. Lundbaek, reference 27.
- Tacchi Venturi, I, 250,轉引自K. Lundbaek, reference 28.
- 括號內為方豪先生夾注。
-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046頁。——方先生所引費文未加引號——筆者。
- A. Pfister, P. 41.
-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1982年北京 / 上海)的利瑪竇條下說:「1589年移居韶州,延師講授《四書章句》,自行意譯成拉丁文,並加注釋。1594年初譯竣。這是《四書》最早的外文譯本。」像該卷其他條目一樣,利瑪竇一條也未附參考文獻目錄,其根據何在,不得而知。
- 39. D. Mungello, P. 250.
- 何高濟先生等根據Louis J. Gallagher的英譯本(書名和出版日期為:China in the Sixteeth Century: the Ja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1953)譯成漢文,書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北京。譯者譯事嚴肅認真,參考了Tacchi Venturi和德禮賢分別編定出版的兩種利瑪竇全集,作了大量注釋,便於讀者了解當時的人物和事件。本文出自該書的引文,基本上直接引用何先生譯本,個別地方根據1615年奧格斯堡拉丁文初版本作了改動。
- Ricci-Trigault, S.29;何譯本第31頁。
- D. Mungello, P.57.
- Ricci-Trigault, S.29;何譯本第31 / 32頁。
- Ricci-Trigault, S.33;何譯本第35頁。
- Ricci-Trigault, S.29;何譯本第31頁。
- Ricci-Trigault, S.33;何譯本第35頁。
- 這三種概念分別見Ricci-Trigault, S. 177、89;何譯本第170、87 / 88頁。
- D. Mungello, P.64.
- Ricci-Trigault, S. 105;何譯本第100 / 101頁。
- Ricci-Trigault, S. 104;何譯本第99頁。
- 同上;何譯本第100頁。
- Ricci-Trigault, S. 109;何譯本第104頁。
- 同上。耶穌的訓誡見《新約•馬太福音》7•12;《新約•路加福音》6•31。
- Ricci-Trigault, S.110-111;何譯本第106頁。
- Ricci-Trigault, S.105;何譯本106頁。
- Ricci-Trigault, S.106;何譯本第101 / 102頁;何譯與筆者譯文差別甚大,這主要是對拉丁文詞substantia(英文:substance)的不同理解造成的。substantia的根本含義是本質,另外也有物質義;通用的英文詞典的第一義項都是物質。但用於哲學,無論是substantia還是英文的substance,其含義都是本體、本體存在、本質。
-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北京,第221頁。
- 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離婁下。
- 《朱子語類》卷18,中華書局版,1986年北京,第398頁。
- 《朱子文集》卷70,轉引自李澤厚,第233頁。
- 《朱子語類》卷94,中華書局版,第2409頁。
- 朱熹:四書集注•中庸•22。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上卷第二篇。
-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北京,第256頁。
- 《孟子•告子上》。
-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 朱熹:四書集注•論語•學而1•1。
- 《朱子語類》卷21,中華書局版,第464頁。
- 同上,第469頁。
- Ricci-Trigault, S. 33;何譯本第35頁。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七篇。
- 轉引自朱謙之,第131頁。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八篇。
- 同上。
- 同上。
- 《新約•路加福音》14•26。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七篇。
- Ricci-Trigault, S. 108;何譯本第103頁。
- 同上。
- 朱熹:四書集注•大學6。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六篇。
- G.E Lessing, Gesammelfe Werke, Aufbau-Verlag, Berlin / Weimar 1968, Bd. 8, S. 612.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七篇。
- 朱熹:玉山講義,轉引自張岱年第219頁。
- 朱熹:明道論性說,轉引自張岱年第219頁。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七篇。
- 同上,第五篇。
- 《荀子•王制篇》。李約瑟先生把亞氏的靈魂階梯說和荀子給人所下的定義列表加以比較,一目了然。他意在證明中西古代哲學思想存在著接觸點。參閱J. Needham, Vol. 2, P. 22。
- 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第七篇。
- 同上,上卷第一篇。
- 93. 94. 同上。
- 安那克薩戈拉(Anaxagoras, 前500-428),希臘哲學家。他認為現實世界的產生是由於無限多的其質各不相同的「原初微粒」(Homoiomerien,原意為相似部分,又譯作「種子」;今從德文Urteilchen,譯作現名)在「奴斯」(Nous),即宇宙理性的作用下所進行的旋渦運動。運動的結果使稀與濃、熱與冷、明與暗、乾與濕分離開來,稀的、熱的、明的、乾的結合為高空;濃的、冷的、暗的、濕的相凝而成大地,從而構成有秩序的宇宙。(而這一切都是「奴斯」安排的。)這種宇宙生成說與朱熹的理氣論很相似,朱熹說:「天地初間只是陽陰之氣。這一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裡面無處出,便結合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他又說:「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朱子語類》卷一,中華書局版,第六頁)萊布尼茨在這兒特別提出安那克薩戈拉,看來並非出於偶然。